节选自《大学堂走出的山大人——山西大学校友故事》文集
这里的赵老师,是北师大文学院教授赵勇,他是我的老师,但在我的眼里,他不仅仅是一位老师,还是——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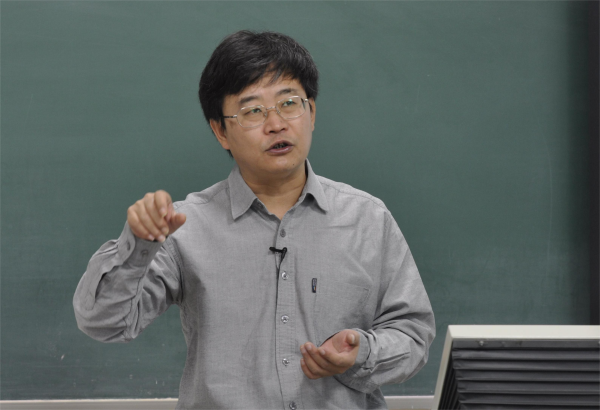
一位会讲故事、能把深奥的文学理论予以欢畅言说的著名学者
我的这种认知产生于2005年10月。那时,我正在读一些与大众文化有关的论著,其中,他的《透视大众文化》和《整合与颠覆:大众文化的辩证法》给了我很大触动。因为它们一点儿不像其他论著那样,摆出一副冷酷的面孔,倔屈聱牙很“康德”,而是通透晓畅、鞭辟入里,处处洋溢着叙述的欢乐。比如,《透视大众文化》对当代影视之“性与暴力”的分析、对冯氏贺岁片“骨灰盒”里秘密的揭示、对广告中欲望诱惑的阐述,都让人有种跋山涉水登顶后一览众山小的舒畅。值得提出的是,这两部著作都是他在读博期间写就的,一部是博士论文,一部是博士论文的副产品,加起来有60多万字。这两部著作,让他从一个与我素不相识的人成了我心中“会写的赵老师”。
凡与赵老师有交往的人,都知其能写会写。2006年9月,长治学院中文系主任曾以老教师赵勇为例与我们新教师谈科研,他说赵勇能写会写,14年发了70多篇文章。他还说,赵勇勤奋有才,1999年去北师大念博士了。14年发70多篇文章,够亮眼!但更亮眼的是,博士毕业后,他平均每年发10篇左右的论文、批评和随笔,其中,被三大文摘转载的有五六十篇;他写作、翻译、编著了《大众媒介与文化变迁》《法兰克福学派内外》《赵树理的幽灵》《大众文化理论新编》《文学与时代的精神状况》等十几部著作,而《大众媒介与文化变迁》和《法兰克福学派内外》还获得过教育部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。2018年,汪民安、李建军在文章中这样说道:“赵勇是国内研究法兰克福学派最有成就的学者之一。”“这些不同来源的材料源源不断……赵勇将它们安置在不同的论述结构中……正是这些不同层面上的材料的支撑,使得他的写作不断递进,在人们似乎感觉到最终的论点呼之欲出之际,一个重要的转折又出现了……这使得赵勇的文章形成了一个递进而繁复的结构,就像复杂的侦探小说一样令人眼花缭乱。”“他最值得注意的特点,还不是这些,而是文体意识的自觉。条畅而雅秀的随笔体表达,将赵勇的‘论文’升华为‘文章’,赋予他的作品以彰明较著的风格和引人入胜的魅力。”这是读了《法兰克福学派内外》《赵树理的幽灵》后,他们发出的由衷感慨。
一名有责任、有担当,甘冒风险与社会战斗,用文字警醒世道人心的知识分子
需要指出的是,这里的“知识分子”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知识人、文化人,而是心中有社稷、眼里有苍生,敢于抵抗现实,具有批判精神的人。这重身份可从他2006—2008 年为《南方都市报》《新京报》《东方早报》《齐鲁晚报》等写的近200篇、30多万字的时评中清晰看出。在那时,他对文化、社会、娱乐、教育、艺术、文学等各个领域发生的有一定影响的事件都进行了及时介入,如南方雪灾事件、黑砖窑事件、作家富豪榜事件、《蜗居》事件、范跑跑事件等都在他的笔下出现过。通过他的及时介入和深度分析,读者不仅知晓了这些事情的来龙去脉,而且看到了隐藏其后的那些影响社会进步和民众觉醒的残酷事实。毫无疑问,在犬儒主义风行、思想淡出的时代,写这些批判性、思想性的文字是不受待见并有风险的,而且也不计入“工作量”,因此,一些学者即使有想法也不去写,而是“两耳不闻窗外事,一心只读圣贤书”。但赵老师没有这样,他义无反顾地投入这种风险写作中,用他的笔、他的智慧和文字写出了他的认识、他的愤怒、他的无奈。难道他不知道这样做有风险? 他当然知道,而且他还知道这样的文字与学术论文不同,是速朽的。但他还是坚持这样做,因为有一种“压在纸背的心情”,警醒世道人心的良知、责任和担当在催动着他。事实上,他并不是2006年才开始这么做的,早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,他就开始了对中国当代文学文化的批判,表露出要说真话的愿望。他的理想,也不是仅仅成为一名“有学问”的学者,还要成为一名知识分子,并在“学者身份和知识分子角色扮演之间取得一种平衡,向往一种自由言说说真话的境界”。因此,他特别推崇赵树理,因为他敢于为民请命; 也异常钟情萨义德,因为他们敢于说真话,向权势说不。
一个朴实诚恳、笃情重义的实在人、有情人
颜小芳在评价《赵树理的幽灵》时,曾用大量篇幅论述赵老师在工作中体现出来的实诚或实受精神。她说,对于赵勇而言,实受“就是不管是讲课还是做研究,他都能贴着真实的生命体验,不浮夸、不空洞,不横空出世、不剑走偏锋,而是有章可依、有迹可循,脚踏实地、循序渐进。”其实,不仅工作中,日常生活中的赵老师也是一个这样的实受人,相信只要读过他那本引起广泛好评的散文集《书里书外的流年碎影》的朋友,都会和我一样,强烈地感受到从他身上迸发出来的那种赤裸裸的、没有丝毫掩饰的深情。他的恩师童庆炳先生很欣赏他的这种为人,曾在多个场合表扬他“不加掩饰”“情信”。他对童老师的感情也非常深。在这里,我想再说两件他和他的老师们的事情。2015年6 月,童老师在金山岭长城过世,这让赵老师极度悲伤。不久, 他写出了首篇忆念恩师的长文《蓝田日暖玉生烟》,字里行间流淌着对恩师的款款深情,读之让人动容。不久,他又写出了第二篇忆念恩师的文章,依旧言辞恳切、情深义重。再后来,他每年都要写几篇与恩师有关的文章。2022年除夕,他还在为恩师的《朴》写书评,他说,只有这么做,“才觉得可以过年了”。不给老师的书写书评就不能过年——只有笃情重义的实受人才会这么做!事实上,他不仅对恩师这样,对其他师友也是如此。《落花无言 人淡如菊》是他追念中国人民大学陈传才老师的一篇文章,从中,我们可感受到他对陈老师感情的那种澄澈。陈老师的学生——河北师范大学邢建昌教授转发此文时说:“厚道而有情谊的赵勇,留下了恩师如此珍贵的照片。”
若细心观察还会发现,三重身份之下,裹着赵老师的一颗“真”心,或者说,他始终在追求“抱朴守真”的生活:剥除语言迷雾是求理论之真,坚持说真话是求事实之真,不加掩饰地用情是求情感之真。那么,他为什么要追求“抱朴守真”的生活?“难得糊涂”不是更好吗?不好。1981—1985年在山西大学求学时,他的老师邢小群、梁归智、程继田等早已对他言传身教——不能走那条路。在一篇写邢小群老师的文章中,他说:“她那颗怀疑、清理、反思乃至批判之心伴随着思想解放的进程,早在20世纪80年代的课堂上就开始萌动了……那是对我们的全面启蒙——文学的、人性的、政治的,甚至人生格调的……现在想来,邢老师的课堂于我而言,就是新启蒙的一个重要场所。”而且,邢老师还直接助力他的处女作在《当代文坛》发表。在回忆梁归智老师的一篇文章中,他也深情叙述了梁老师对他的影响:“梁老师也笑了,但是当他收起笑容开讲《窦娥冤》时,却是对悲剧的严肃反思:从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,西方世界的悲剧观是怎样发展的,为什么中国古代的悲剧喜欢有一个‘大团圆’结局,恐惧与怜悯究竟是怎么回事,‘善恶相报’何以具有反悲剧色彩……它对我的启迪也依然至关重要,因为悲剧问题是我学术研究的起点。”
这么说来,赵老师“抱朴守真”的生活方式上是盖着一个大大的“山西大学”印章的,是它影响了他,成就了他。
魏建亮,河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

